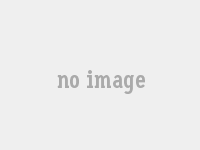一、“大同世界”、“协和万邦”、“亲仁善邻”,请问古代思想家提出的那些思想和这个理念相符合
一、“大同世界”指: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,人人爱幼,无处不均匀,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
源自《礼记·礼运》篇,其中有对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描述:“ 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……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”
二、“协和万邦”指的是:坚持互信、互利、平等、协商、尊重多样文明、谋求共同发展,强调求同存异、合作共赢。
在2018年6月9日,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欢迎宴会并致辞。
源自于中国古老的经典《尚书》,提出“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”的理想,主张人民和睦相处,国家友好往来。
三、“亲任善邻”指:与邻者亲近,与邻邦友好。
源自于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:“往岁, 郑伯 请成于 陈 , 陈侯 不许。 五父 谏曰:‘亲仁善邻,国之宝也,君其许 郑 。’”
扩展资料: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,历来追求和睦、爱好和平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“亲仁善邻,协和万邦”,不仅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“仁”、“和”的优秀基因,也体现了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广阔胸怀。
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,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。如今各国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加,只有尊重、包容不同文明的存在,坚持互利合作,纳百家优长,集八方精义,才能与世界各国一道,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。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大同世界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协和万邦
参考资料来源:百度百科-亲仁善邻
二、郑州万邦离昆明开车多久
驾车路线:全程约1922.5公里,历时27-30小时
起点:万邦物流园
1.郑州市内驾车方案
1) 从起点向正南方向出发,行驶80米,右转进入万洪路
2) 沿万洪路行驶3.0公里,左转
3) 行驶5.1公里,直行
4) 行驶1.4公里,右前方转弯进入郑民高速公路
5) 沿郑民高速公路行驶7.0公里,朝新乡/机场/北京/武汉方向,稍向右转进入祥云寺枢纽
2.沿祥云寺枢纽行驶1.7公里,过祥云寺枢纽,右前方转弯进入京港澳高速公路
3.沿京港澳高速公路行驶77.0公里,过清潩河桥,朝登封/南阳/S32/S83方向,稍向右转上匝道
4.沿匝道行驶1.1公里,直行进入永登高速公路
5.沿永登高速公路行驶11.9公里,朝平顶山/南阳/S83方向,稍向左转进入兰南高速公路
6.沿兰南高速公路行驶770米,直行进入兰南高速公路
7.沿兰南高速公路行驶167.1公里,朝邓州/G55/襄樊方向,稍向右转进入二广高速公路
8.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1.0公里,过陈官营枢纽,直行进入二广高速公路
9.沿二广高速公路行驶465.9公里,朝张家界/常德北/太阳山/G5513方向,稍向右转上匝道
10.沿匝道行驶430米,直行进入杭瑞高速公路
11.沿杭瑞高速公路行驶262.8公里,朝凤凰/怀化/广州/瑞丽方向,稍向右转进入杭瑞高速公路
12.沿杭瑞高速公路行驶960米,直行进入包茂高速公路
13.沿包茂高速公路行驶34.3公里,朝凤凰/铜仁/G209方向,稍向右转进入杭瑞高速公路
14.沿杭瑞高速公路行驶630米,直行进入杭瑞高速公路
15.沿杭瑞高速公路行驶117.8公里,在闵孝/S303出口,稍向右转上匝道
16.沿匝道行驶930米,直行进入安江高速公路
17.沿安江高速公路行驶140.8公里,直行进入贵瓮高速公路
18.沿贵瓮高速公路行驶71.0公里,稍向右转进入贵瓮高速公路
19.沿贵瓮高速公路行驶1.9公里,直行进入贵瓮高速公路
20.沿贵瓮高速公路行驶16.0公里,朝白云/观山湖/六盘水/安顺方向,稍向右转上匝道
21.沿匝道行驶1.4公里,直行进入贵阳绕城高速公路
22.沿贵阳绕城高速公路行驶34.7公里,过小箐大桥,朝清镇/安顺/昆明/G60方向,稍向右转上匝道
23.沿匝道行驶790米,直行进入沪昆高速公路
24.沿沪昆高速公路行驶360.5公里,过白石江桥,直行进入杭瑞高速公路
25.沿杭瑞高速公路行驶128.7公里,在北京路/龙泉路/北辰大道/白云路出口,稍向右转上匝道
26.沿匝道行驶440米,过小庄立交桥,右前方转弯进入二环北路
27.昆明市内驾车方案
1) 沿二环北路行驶540米,直行进入二环北路
2) 沿二环北路行驶250米,过金星立交桥,在第3个出口,左转进入北京路
3) 沿北京路行驶3.7公里,过左侧的中房大厦约130米后,左转进入东风东路
4) 沿东风东路行驶240米,到达终点(在道路右侧)
终点:昆明市
三、夫子曰:好美如好缁衣,恶恶如恶巷伯,则民臧秘而刑不屯 。《诗》云:“仪刑文王,万邦作孚。”
释郭店简《缁衣》①
——以今本《礼记·缁衣》为参照
(主要依据涂宗流 刘祖信 《郭店楚简《缁衣》①通释》下简称为“涂刘按”,另参照刘信芳:《郭店简〈缁衣〉解诂》;周桂钿:《〈郭店楚墓竹简·缁衣〉研究札记》;李零: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;廖名春:《新出楚简试论》)
一 夫子曰:好美如好缁衣,恶恶如恶巷伯②,则民臧秘而刑不屯 ③。《诗》云:“仪刑文王,万邦作孚。” ④
①涂刘按:郭店楚简《缁衣》(以下称简本)与《礼记•缁衣》(以下称今本),其内容大体相合,应是同一文本的不同传本。简本无今本的第一及第十六两章。章序有很大不同,文字也有不少出入。
按:
简本《缁衣》无今本第一章,即“子言之曰:‘为上易事也,为下易知也,则刑不烦矣。’”
也无今本第十六章,即子曰:“小人溺于水,君子溺于口,大人溺于民,皆在其所亵也。夫水近于人而溺人;德易狎而难亲也,易以溺人;口费而烦,易出难悔,易以溺人;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,可敬不可慢,易以溺人。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。太甲曰:‘毋越厥命,以自覆也。若虞机张,往省括于厥度则释。’兑命曰:‘惟口起羞,惟甲胄起兵,惟衣裳在笥,惟干戈省厥躬。’太甲曰:‘天作孽,可违也。自作孽,不可以以逭。’尹吉曰:‘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,自周有终,相亦惟终。’”
另简本《缁衣》第十八章无今本“子曰:‘下之事上也,身不正、言不信则义不壹、行无类也。’”
第九章, 今本“从容有常”后,有“以齐其民”一句,未见於竹简。又今本引《诗》云:“彼都人士,狐裘黄黄。其容不改,出言有章。行归于周,万民所望。”较竹简引《诗》多出三句。犹为重要的是,今《彼都人士》之首章以“黄、章、望”韵(阳部),而竹简所引以“引、信”韵 (真部),这已不是一般的异文问题,具体原因,有待进一步研究。 (郭店简《缁衣》解诂 作者:刘信芳 )
郭店楚简本第五章只引《诗•小雅•节南山》“隹秉�成,不自为贞,卒�百眚”三句,而《礼记•缁衣》篇在这三句前却多出“昔吾有先正,其言明且清。国家以宁,都邑以成,庶民以生”五句逸《诗》,从体例上看,此处逸《诗》当为后人窜入。郭店楚简本第十二章引“寺员:�大夫共��,林人不�”两句,既不见於《诗经》,也不见於它书,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一书认为当属逸《诗》,其说是。《礼记•缁衣》篇於此章只引《尚书•甫刑》,没有引《诗》。(廖名春《新出楚简试论》)
尽管简本《缁衣》与今本《缁衣》内容大致相同,但是其排列次序却大相迥异(除了简本无今本第一章的原因之外),排列位置相同的只有六、九、十三、十八四章。
② “美”,今本作“贤”。刘信芳按:《释文》引郑《目录》:“善其好贤者之厚,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也。《缁衣》,郑诗美武公也。
按:
“如好缁衣,如恶巷伯”,今本脱“好”“恶”二字。缁衣,出自《诗•国风•郑风•缁衣》。可参看《毛诗序》:“《缁衣》,美武公也。父子并为周司徒,善于其职,国人宜之,故美其德,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。”《笺》:“父谓武公父桓公也。司徒之掌十二教,‘善善者’,治之有功也。郑国之人皆谓桓公、武公居司徒之官,正得其宜。”
巷伯,出自《诗•小雅•小昊之什•巷伯》,参看《毛诗序》:“《巷伯》,刺幽王也。寺人伤于谗,故作是诗也。”《笺》:“巷伯,奄官。寺人,内小臣也。奄官上士四人,掌王后之命,于宫中为近,故谓之‘巷伯’,与寺人之官相近。谗人谮寺人,寺人又伤其将及巷伯,故以名篇。”
疑此处的谗人应为巷伯。根据巷伯之诗,似乎是巷伯欲与寺人图谋不轨之事,而寺人不从,故巷伯进谗言陷害之,以免其阴谋败露。故诗之结尾曰:寺人孟子,作为此诗。凡百君子,敬而听之。表达了对巷伯之流的愤怒与无奈之情。
③“则民臧秘而刑不屯”,今本作“则爵不渎而民作愿,刑不试而民咸服”。
信芳按:《说文》“秘”字云:“权度多少中其节谓之秘。”盖执政者好恶分明,则民知其节度而秘择之,此“臧祔”之谓。孔子认为,国君能效法先王,民知贵贱之度,则国治而有序(参下引)。是“臧祔”之引申义,谓民顺适君王之好恶,以别贵贱善恶之度也。从刘说。
臧秘,查《辞源》,臧有善,奴隶,贿赂或盗窃之物,姓,收藏五个义项;秘则有神(即神秘不可测之意),隐密,希奇,闭四个义项。根据句意,另据刘信芳的注释,似有民于其君之好恶而知节度,自觉扬善而隐恶之意。
另按李零说法,“臧秘”读作“咸力”,力即尽力、竭力的意思。李零此处校读可能是参照了今本的“刑不试而民咸服”,符合今本之意。可备一说。
刑,李零读为“型”,注曰:“型”,原作“刑”,下文引诗有“仪型”之语,这里的“刑”是相应于《诗》,应读为“型”。但参看今本,刑乃刑罚之意,更贴近原意。所以,仍读作“刑”。
屯,今本读作“试”。刘信芳按:字形之误也。《离骚》:“屯余车其千乘兮。”王逸注:“屯,陈也。”春秋时多铸刑器,《左传》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书,叔向云:“今吾子相郑国,作封洫,立谤政,制参辟,铸刑书,将以靖民,不亦难乎?《诗》曰:仪式刑文王之德,日靖四方。又曰:仪刑文王,万邦作孚。如是何辟之有。民知争端矣,将弃礼而征於书。”……且叔向所引之《诗》,亦见《缁衣》所引。可知简文“刑不屯”即“刑不陈”。今本作“刑不试”,自汉迄今,误之久矣。从刘说。
④诗云,今本作“大雅曰”。万邦,今本作“万国”。“《诗》云”引文见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,“邢”,法也。孚,相信。言惟效法文王,才能赢得万邦信任。涂刘按:今本避汉高祖讳改“邦”为“国”,可证今本抄定于汉初。
释:该章为今本第二章。孔子说:“如果君主爱好贤能如《缁衣》中所描述的那样,憎恶谗人能如《巷伯》中所描述的那样,那么人民就会知善恶之度,主动隐恶扬善,刑罚也就不需要陈设。《诗》上说“(仪容)惟效法文王,才能赢得万邦信任”。
二 子曰:有国者章好章恶①以视民厚,则民情不忒② 。《诗》云:“靖共尔位,好是正直。”③
① “章好章恶”,今本作“章善瘅恶”。
涂刘按:“好”改为“善”,使夫子口语变为书 面语,失去特色。“瘅”,病也。
刘信芳按:作“善”作“义”者皆非(指“好”字),有如竹简本第一章“美”,汉儒改作“贤”。孔子所述,原本平易近人 ,故用“美”,用“好”,汉儒改“美”为“贤”,改“好”为“善”、为“义”,用字虽典雅,然已使夫子之口头语变成了书面语,似是而非矣。“章”者,明也,经典多用“彰”。 《书·尧典》“平章百姓”注疏:“明也。”从刘说。
按:“瘅”,查古汉语字典,有因积劳成病,憎恨,炽热、炎热和热症四个义项。根据今本之意,“章善瘅恶”中的“瘅”同“章”相对,应为动词,作憎恨讲。涂刘的解释疑有误。
②视,今本作“示”,忒,今本作“贰”。涂刘按:“视”、“示”两字通。“民情不忒”, “忒”原释文作“弋”,今本作“贰”,依“裘按”定为“忒”。
刘信芳按:汉儒所传之本或作“视”,递省作“示”。厚,《礼记·坊记》“以厚别也”。郑注:“厚,犹远也。”盖章好章恶则善恶之分也远矣,民是以知从善而远恶。忒,《郭店》释“弋”,裘按释“忒”,裘说是也。今本作“贰”,《释文》或作“忒”。 《诗·曹风·?鸠》“其仪不忒”毛传:“忒,疑也。”
按:
《论语·学而》“曾子曰:‘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’” 此处意为忠厚老实或仁慈宽厚。似与“以视民厚”意义相符。
《论语·卫灵公》“子曰: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,则远怨矣。’”此处意为多或严厉之意。
《大学》“其本乱而末治者,否矣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,未之有也。”此处有重视看重之意,厚者指代家。
《坊记》“ 子云:‘父子不同位,以厚敬也。’”此处厚亦有重视之意。
“子云:‘父母在,不称老,言孝不言慈;闺门之内,戏而不叹。君子以此坊 民,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。’” 亦是重视之意。
“子云:‘取妻不取同姓,以厚别也。故买妾不知其姓,则卜之。以此坊民, 鲁《春秋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,其死曰孟子卒。’”此处的厚别,元陈澔注:厚其有别之礼。根据句意,似应释为重视这种有别之礼,恐非刘信芳所引述郑注所言“远”之意。
“子云:‘寡妇之子,不有见焉,则弗友也,君子以辟远也。故朋友之交,主 人不在,不有大故,则不入其门。以此坊民,民犹以色厚于德。’”亦是重视之意。
《中庸》“ 继绝世,举废国,治乱持危,朝聘以时,厚往而薄来,所以怀诸侯也。”厚往薄来,陈澔注:谓燕赐厚而纳贡薄。
“故至诚无息。不息则久,久则征;征则悠远,悠远则博厚,博厚则高明。”此处的厚是深厚、笃厚之意。
“故君子尊德性,而道问学,致广大,而尽精微,极高明,而道中庸。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”据朱熹注:敦,加厚也。此处的厚应是深厚笃厚之意。
《表记》“仁者 人也,道者义也。厚于仁者薄于义,亲而不尊;厚于义者薄于仁,尊而不亲。”此处厚意为偏重。
“子曰:下之事上也,虽有庇民之大德,不敢有君民之心,仁之厚也。”此处厚意为宽厚笃厚。
“子曰:先王谥以尊名,节以一惠,耻名之浮于行也。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, 不自尚其功,以求处情;过行弗率,以求处厚;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,以求下贤。 是故君子虽自卑,而民敬尊之。” 此处厚有笃厚之意。
“子言之曰:后世虽有作者,虞帝弗可及也已矣;君天下,生无私,死不厚其 子;” 此处厚指偏袒、厚爱之意。
“子曰:事君,军旅不辟难,朝廷不辞贱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,则乱也。故君使其臣得志,则慎虑而从之;否,则孰虑而从之,终事而退,臣之厚也。《易》 曰:‘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’”此处厚意为忠厚笃厚。
综之,“以视民厚”之厚,应为仁慈宽厚或忠厚笃厚之意为佳。
③“《诗》云”,出自《诗·小雅·小明》。靖,安定。共,通“恭”,恭敬。好是正直,爱此正直之人。
释:该章为今本第十一章。孔子说:有国者应该向人民彰显好恶,以便使人民看到你的仁慈宽厚,那么民情就会朴实专一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安静恭谨地居于你的位置,爱好正直之人。”
三 子曰:为上可望而知也,为下可类而等也①,则君不疑其臣,臣不惑于君②。《诗》云:“淑人君子,其仪不忒。”《尹诰》云:“惟伊 尹及汤,咸有一德。” ③
①为下可类而等,今本作“为下可述而志”。刘信芳按:按“述”古读如“遂”,与“类”音近。“等”字从竹寺,而“寺”与“志”音近,“述而志也”当是传钞之讹。该句《郭店》依旧本读,裘按读“类而等也”,裘说是也。
②君不疑其臣,今本作“君不疑于其臣”,“于”字衍;臣不惑于君,今本作“而臣不惑于其君矣”,“其”“矣”字衍。信芳按:臣不被君所惑者,为君言行 明确,“可望而知”,可听而明也。君不疑其臣者,为臣类有等差,君尽其材而用之,故不疑也。
③简本“《诗》云”在前“《尹诰》”在后,今本错位。“《诗》云”出自《诗·曹风·鸤鸠》,仪,仪容。涂刘按:《尹诰》,《尚书》篇 名 ,今本误为“尹吉”。此章《尹诰》引文,已为今本《尚书•咸有一德》采入。今本“尹躬 ”,当读为“伊尹”。另周桂钿按:尹躬,读作“伊尹”,不妥。尹,是伊尹的尹。躬,指本身,本人。这句话是说伊尹与汤的君臣关系融洽,都有相应的道德。指相互信任,相互配合。蔡沈注:一德,纯一之德,不杂不息之义,即上文所谓常德也。
释:该章为今本第十章。孔子说:作为君主可以言行明确,一望而知,作为臣子可以明确其等差(君主方能尽其材而用之),那么君主就不怀疑其臣,臣子也不会被君迷惑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善良的君子,他的威仪不变色。”《尹诰》上说:“惟伊尹和成汤君臣,都具有纯一之德。”
四 子曰:上人疑则百姓惑,下难知则君长劳。故君民者章好以视民欲① ,谨恶以渫民淫,则民不惑②。臣事君,言其所不能,不诒其所能,则君不劳③。《大雅》云:“上帝板板 ,下民卒瘅。” ④《小雅》云:“非其止之,共维王恭。” ⑤
①今本第十二章。以视民欲,今本作“以示民俗”。按:此处可与上句“以视民厚”相参照,上句中“厚”经考辨释为君主的仁慈宽厚,则此处的“欲”应释为君主的个人欲求。
②谨恶以渫民淫,民不惑,今本作“慎恶以御民之淫,则民不惑矣”。渫,裘锡圭按:该字与《穷达以时》第二号简“?”字右旁相同,似当释为“渫”,《说文》:“渫, 除去也。”李零按:“?”读为“御”。“御”原从水从亡,裘案以为是表示除去之义的“渫”字。案此字从亡,为阳部字,疑以音近借为“御”,今本作“御”。可备一说。
③臣事君,言其所不能,不诒其所能,则君不劳,今本作“臣仪行,不重辞,不援其所不及,不烦其所不知,则君不劳矣。” 。刘信芳按:诒,《说文》:“诒,相欺诒也。”上文云“下难知则君长劳”,此则言臣事君,既言其所不能,亦明其所能,上易知臣,如是则君不劳矣。《郭店》释“诒”为“词”,裘按读为“辞”。其实该字可以直接隶定作“诒”。从刘说。
④“《大雅》云”,今本作“诗云”,出自《诗·大雅·板》。《毛诗序》:“板,凡伯刺厉王也。”《笺》:“凡伯,周同姓,周公之胤也,入为王卿士。” ”。板板,反常。瘅,今本作“■”(左“疒”右“澶”之右)。《说文》:“瘅,劳病也。”
⑤非其止之,共维王恭,今本作“匪其止共,惟王之邛”,出自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。《毛诗序》:“巧言,刺幽王也。大夫伤于谗,故作是诗也。”
陈澔注:邛,病也,言此谗人非止于敬,徒为王之邛病耳。《板》诗证君道之失,《巧言》诗证臣道之失也。
刘信芳按:(依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)盖言失却真诚,则“盟”也好,“信”也好,“甘”也好,徒为欺诈。并非要止“盟”,止“信”,止“甘”(此依竹简“止之”作解),治国之道,全在於王之肃慎而已。竹简本引《诗》云:“非其止之,共唯王恭。”与今本不同,“共”,同也。“共唯王恭”,文从字顺。
李零按:“非其止共,唯王之邛”,简文“共唯王”与“之”字互倒,今为乙正。
按:从简本该句的行文来看,陈澔和李零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。简本首言“上人疑则百姓惑”,即君道;再言“下难知则君长劳”,即臣道。后面则是对其的详解。如是,则后面引《诗》亦应分述君道与臣道。而根据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内容,所谓的君子,可以理解为臣子。则“非其止之,共维王恭”,就是今本的的
“非其止共,唯王之邛”,引此以证臣道之失,与上文呼应。只是在止的主语上,根据文意,似应是臣子,而非谗人。因为这里讲的是臣道,如果释为谗人,则不仅仅是讲臣道了。
释:该章为今本第十二章。孔子说:君主多疑则百姓困惑,臣子难知则君主劳烦。所以君主应该彰显所好以使人民看到自己的欲求,谨防邪恶以便荡涤去人民的迷乱,则人民就不会困惑。臣子侍奉君主,既言其所不能,亦明其所能,上易知臣,如是则君不劳矣。《大雅》上说:“上帝反戾,那么下民就会劳苦。”《小雅》上说:“臣子若非止于恭敬,那么就只会成为君主的邛病。”
五 子曰:民以君为心,君以民为体。心好则体安之①,君好则民裕之 ②。故心以体废③,君以民亡。④ 《诗》云:“谁秉国成,不自为正,卒劳百姓。”⑤《君牙》云 :“日溶雨,小民惟日怨。晋冬耆沧,小民亦惟怨。” ⑥
①心好则体安之,今本作“心庄则体舒,心肃则容敬,心好之身必安之。”
②君好则民裕之,今本作“君好之,民必欲之”。刘信芳按: 或据此谓“?”读为“欲”,疑非是。盖“?”与上文“安”相照应,应读为“裕”,宽也。……盖君“好”,民乃得宽松也。从刘说。
③心以体废,今本作“心以体全,亦以体伤”。裘按:“废”,简文作“法”,疑当读为“废”,二字古通。今从。另刘信芳按:按“心以体法”与上文“君以民为体”相照应,是谓为君治国之法,本之於民。其行文结构,明显优於今本。或读“法”为“废”,非是。法者,模也,范也。
④“君以民亡”,今本作“君以民存,亦以民亡。”
⑤“《诗》云”引文,出自《诗·小雅·节南山》,今本还有“昔吾有先正,其言明且清。国家以宁,都邑以 成,庶民以生”。正,《节南山》作“政”。
⑥《君牙》,今本为《君雅》,引文今本作“夏日暑雨,小民惟曰怨,资冬祈寒 ,小民亦惟曰怨”。刘信芳按:简文“牙”与《说文》“牙”之古文同。《君牙》旨在说明小民埋怨天气,原因在于夏雨冬寒,以喻民之冷暖系於君王,是君民者可不慎欤!
四、处中国以治万邦的意思?
看了许多文章,大都集中探讨解释中国一词的历史意义何时出现。在我看来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,完全背离了中华特有的历史思想规律。此话核心的思想是中华文明渊源之所在,即何为中华文明之正统。
首先理解这句话,必须清楚此话所处的时代背景,相关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,以及这句话所折射的特定的历史常识。
第一,时代背景。我们来看此话的出处,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:姜伯约归降孔明,武乡侯骂死王朗。王司徒滔滔不绝信心满满的自以为是,换来的是一口鲜血栽与马下,诸葛孔明谈笑间敌人血染疆场,换来了一段千古佳话名留清史。相信这个名场面熟悉三国的都清楚,双方言辞之睿智、碰撞之激烈,相信各有体会判断,再此不多赘述。
我们单就王朗此话到底在透露什么讯息为主要线索,去探讨中国自古之文人士子的思维逻辑。诸葛亮此次北伐,曹丕已经称帝,注意是汉献帝禅位,这是有历史依据的,法尧禅舜。并且定都城在洛阳。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曹魏篡汉为何要定都洛阳? 而不是曹氏家族之中兴之地邺城?
再看洛阳在三国历史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,纵观中华名族古代史,夏朝古都斟鄩,也就是洛阳盆地附近。商定都毫今河南商丘,东周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,东汉也定都与洛阳,即使秦统一以及西汉初立,洛阳也一直作为实质意义上的陪都存在,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,洛阳在早期中华朝代更替中,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何也?
第二,这就说道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。而中原文明的代表既是河洛文明。我们说除了夏商时代有未定的因素外,可以确定的是,中华思想文明最辉煌灿烂的时期是东周,并一直持续500年之久。东周一直定都洛阳,期间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。直接造就了后世几千年文明之基业。我们熟知的儒家道家代表人物孔子老子。他们思想碰撞的所在地也正是洛阳。政治上建都于此,文化上思想家汇集于此,经济上中原地区也在当时一直是经济枢纽。这足以证明河洛文明既是代表中华文明之正统。至少在三国之前是这样的。
再此,需要补充讲一点,战国为何最终完成统一的是秦国,而不是中原其他国呢?我们知道当时实行变法的不只秦国,其他诸侯各国都实行过并取得了一定成就。其他深层次原因抛开不详谈,我们不得不考虑重要因素之一就是,中原各国受中华文明影响太深,传统思想束缚太重,最终不敌边陲之秦国。
第三,三国时期之母国两汉关于定都的考虑,西汉建立之初对于定都君臣之间是有激烈的争论的。刘邦主张建都洛阳这个当时经济繁荣地区富足的都城的,而张良娄敬则主张关中立都。为何呢?这就与当时中原地区形势不明朗,恐各诸侯有变,从政治安全考虑,军事上战略回旋余地来讲,关中是第一选择。
这其中娄敬就尖锐的指出为何不定都洛阳,娄敬说曰:“陛下都洛阳,岂欲与周室比隆哉?”上曰:“然。”娄敬曰:“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。周之先自后稷,尧封之邰,积德累善十有馀世。此话怎么讲呢,直白点就是,周室500年基业打下的群众基础,岂是你小小泗水亭长能比拟的。这就看出当时中原正统文明的根深蒂固不可轻易撼动。
我们延伸一下中原文明之深远影响。三国之后魏晋南北朝,彼时中原大乱,直接后果就是衣冠南渡,中原文人士子士族豪强进行了大规模南迁,而中原士族与南方士族迅速达成政治互信,直接或间接建立了宋齐梁陈四朝。虽然乱世使得经济文化中心难移,但是追根溯源,一直都有中原文明的或明或暗的影响。从后来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五代十国以后,中华文明之所以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得以延续的文明,没有被外族文明消灭,反而真相学习中原文明被最终同化。不得不说,中原文明生命力之强大。
最后,正统的重要性,回到这句话,处中国以治万邦。何解?如何使万邦来朝呢?政治地位的象征意义,文明的先进程度,经济的繁荣程度。而当时的中原即中国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。换句话说洛阳就是中原文明的象征。
自古得中原(中国)者得天下,群雄逐鹿中原,这都是经过历史验证的恒之不变的真理,彼时曹魏具天时地利人和(虽然人和有疑问,相对来说曹魏在当时确实是最强大的),王朗此言实在并不为虚。也不难理解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。何况历史上真实的王朗是曹魏重臣经学家。从未被什么孔明之流骂死。